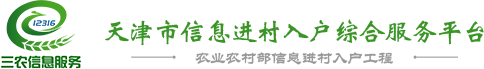近代是中国文学的转型时期,小说从传统转向现代,在此大潮中,天津不仅出现了志怪小说、话本小说等优秀之作,还出现了新的小说理论,成为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先声,为近代天津新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作为洋务运动的策源地,天津城市的各方面都逐渐走在了时代的前列。19世纪八九十年代,津门人才汇聚,思想活跃,任职于北洋水师学堂的严复,1895年在天津《直报》发表的一系列文章,如《论世变之亟》《原强》《救亡决论》《辟韩》等,成为维新变法的新声,引领了一个时代。1897年,严复与王修植、夏曾佑、杭辛斋在天津创办《国闻报》,成为维新派在华北地区创办的第一张日报,影响力极大。《国闻报》志在求通,一是通上下之情,二是通中外之故。1897年11月,严复、夏曾佑在《国闻报》连载了一篇文章《本馆附印说部缘起》,这篇小说文论的意义有多大呢?概括而言,它代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小说理论,使当时的天津文学即将站到20世纪文学的前列!
这篇文论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:一是认识到小说具有影响和左右社会民心的重要作用,应该对其加以重视;二是认识到小说具有通俗易懂、利于传播的优点,可以成为传播新思想的载体;三是大力批判中国传统小说,认为那些都是志兵、志盗、言情之作,危害社会。由此,国闻报馆想要仿效欧美、日本等国家,翻译新小说,借小说之力使民开化。
虽然严复、夏曾佑翻译和附印小说的计划没有实施,但其理论为后来小说语言的通俗化、内容的革新指明了方向,对近代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梁启超曾说:“天津《国闻报》初出时,有一雄文,曰《本馆附印说部缘起》,殆万余言,实成于几道(严复)与别士(夏曾佑)二人之手。余当时狂爱之,后竟不克裒集。”《缘起》中的主要思想被梁启超所吸收,在其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(刊于1902年《新小说》第一号)中有所体现,进一步强调小说的地位,发挥小说在社会改革中的作用,提出“欲新一国之民,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”的理论,引领了20世纪初轰轰烈烈的小说界革命。
小说界革命开始之后,天津文学界同样有所响应。笔者在1906年的《大公报》上发现一篇津门张蔚臣的来稿《拟立广智小说会社议》,文中说小说感人最深,可以移风易俗,计划择泰西政治、日本维新诸小说,或李提摩太所译之泰西新史,变通而演说之,这样有利于民众的人格养成,“扩其思想,开其智识,动其感情”,由此成立广智小说会。当然,近代天津新小说的成就不只是在理论方面,还有其丰富的新小说作品。